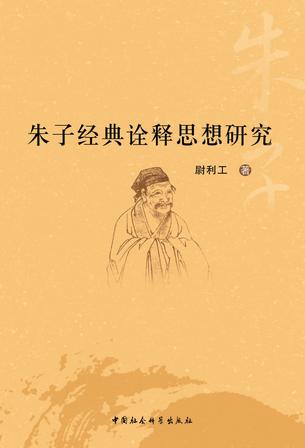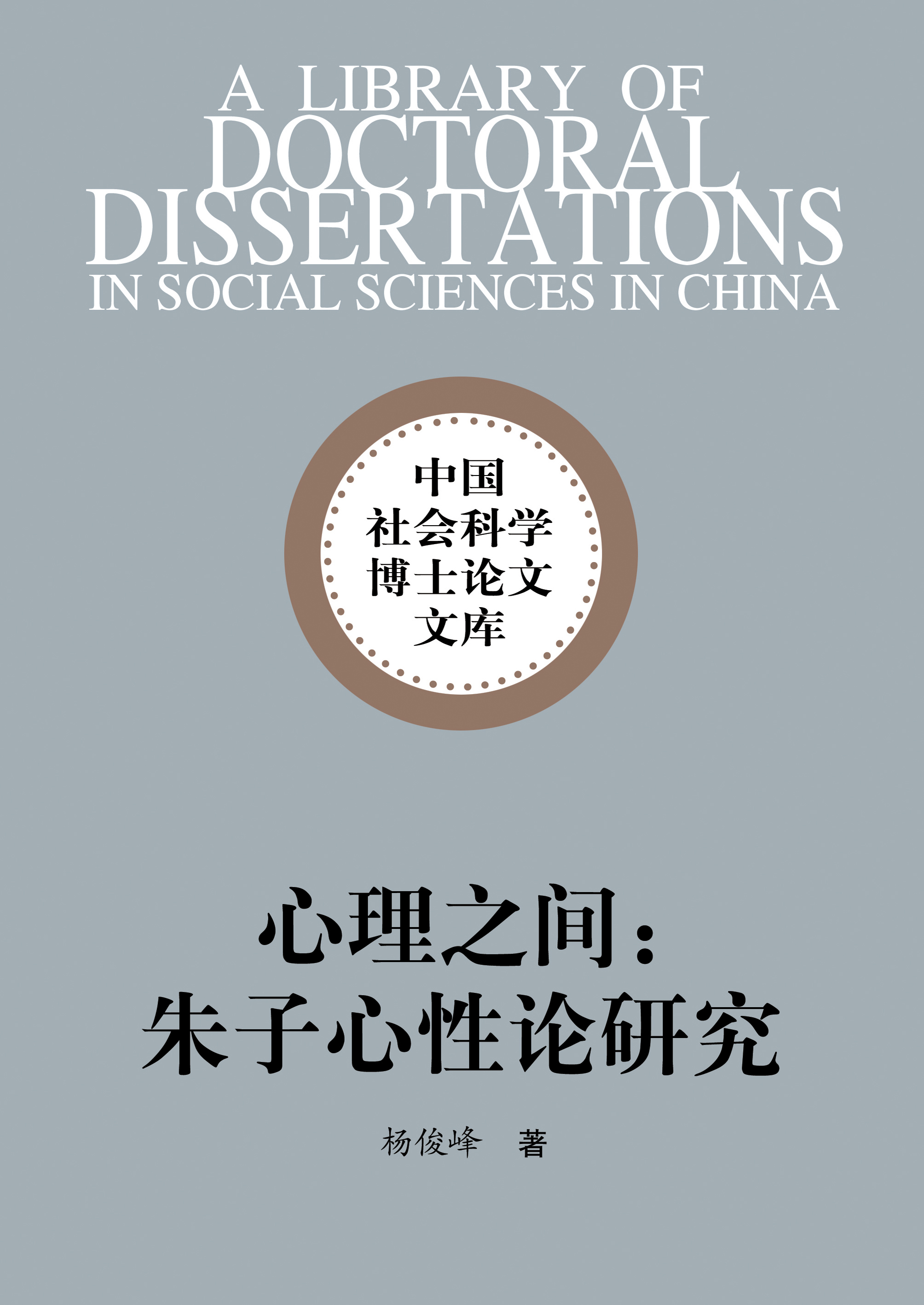内容简介
作者简介
目录
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彭国翔正如儒学早已不再是中国人的专利一样,儒学研究也早已成为一项全世界各国学者都在参与的人类共业。“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态”不可避免地导致固步自封,落后于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具有国际的视野,“闭门造车”充其量也不过是“出门合辙”,难以真正推陈出新,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如今,理、工、农、医以及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无不步西方后尘,已是无可奈何之事,不是“赶英超美”的豪情壮志所能立刻迎头赶上的。至于中国传统人文学包括文、史、哲的研究,由于晚清以至20世纪80年代不断激化的反传统思潮在广大知识人群体中造成的那种“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普遍心态,较之“外人”的研究,也早已并无优势可言。中国人文研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再出发”,至少在中国大陆,已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了。依我之见,现代意义上中国人文学研究的鼎盛时期是在20世纪20—40年代。尽管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但学术研究并未受到意识形态的宰制,一时间大师云集、硕儒辈出。而那些中国人文学研究的一线人物,除了深入中国古典、旧学之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通他国语文,能够及时了解和吸收域外中国人文研究的动态与成果。所谓“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不但是“学衡派”诸君子以及当时那些大师硕儒的标的,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恰恰是他们自己学行的体现。1949年鼎革之后,虽然有一批人文硕儒避地海外,于“花果飘零”之际,使现代中国人文研究的传统得以薪火相传,但毕竟难以维持以往的鼎盛了。如今中国大陆人文研究的再出发能否趋于正途、继往开来,在一定意义上,其实就是看能否接得上20世纪20—40年代的“学统”。接续并发扬现代中国人文研究学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及时了解和吸收海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此,中国人文学界的知识人其实不乏自觉。单纯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自清末民初以来已经蔚为大观,这一点自不必论。海外研究中国人文学术的各种著作,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渐成风潮,以至于“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几乎成为一个独立的园地。不过,对于“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本身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笔者历来是有所保留的。很简单,海外有关中国人文研究的各种成果,无论采用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或“经、史、子、集”,还是现代的“文、史、哲”,都必然系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学科部门。而鉴别这些研究成果的高下、深浅和得失,必须得是该学科部门的当行人士,绝不是外行人士所能轻易置评的。譬如,一部西方学者用英文撰写的研究苏轼的著作,只能由那些不仅通晓英文同时更是苏轼专家的学者才能论其短长,我们很难想象,在文学、历史、哲学、宗教、艺术等人文学科的部门和领域之外,可以有一个独立的“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如果本身不是中国人文学科任何一个部门的专业人士,无论外国语文掌握到何种程度,都很难成为一位研究海外或国际汉学的专家。所谓“海外汉学”或“国际汉学”并不能构成独立于中国人文学之外的一个专门领域,其意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海外,无论“汉学”还是“中国研究”,正是一个由包括历史、哲学、宗教、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各门具体学科构成的园地,而不是独立于那些学科之外的一门专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要想真正了解和吸收海外中国人文研究的最新成果,还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了解和吸收的主体自身,必须是中国人文学相关领域的内行人士,对于相关海外研究成果所处理的中国人文课题的原始文献,必须掌握娴熟,了解其自身的脉络和问题意识。只有如此,了解和吸收海外的研究成果,才不会导致盲目的“从人脚跟转”。否则的话,非但不能对海外中国人文研究的成果具备真正的判断力和鉴赏力,更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为我所用了。当前,在中文世界中国人文研究的领域中,也出现了一股对西方学者的研究亦步亦趋的风气。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人文的研究稍有风吹草动,中文世界都不乏聪明才智之士闻风而起。但各种方法、模式和理论模仿得无论怎样惟妙惟肖,是否能够施之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对象而“有用武之地”,不至于生吞活剥,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质。所谓“法无定法”,任何一种方法本身并无所谓长短高下之分,其运用的成功与否,完全要看是否适用于研究对象。譬如,在北美的中国史研究中,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目前似乎已经式微,起而代之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地方史(local history)等研究取径颇有独领风骚之势。但是,如果研究的对象是宋明时代一位或一些与其他各地学者经常保持联系的儒家知识人,那么,即使这位儒家学者多年家居并致力于地方文化的建设,这位或这些学者与其背后广泛的儒家士人群体的互动,以及那些互动对于这位学者观念和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需要充分考虑,这就不是单纯的地方史的研究取径所能专擅的了。再者,如果要了解这位或这些学者思想观念的义理内涵,社会史的角度就难免有其盲点了。如今,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文学的研究,所可虑者似乎已经不是对于海外研究成果缺乏足够的信息,反倒正是由于对各种原始文献掌握不够深入而一味模仿西方学者研究方法、解释模式所产生的“邯郸学步”与“东施效颦”。中国人文学研究似乎正在丧失其主体性而落入“喧宾夺主”的境地尚不自知。然而,面对这种情况,是否我们就应该采取“一刀两断”的方式,摈弃对于海外中国人文学术的了解和引进,如此才能建立中国人文研究的主体性呢?显然不行,那势必“自小门户”,不但不能接续20世纪20—40年代所形成的良好学统,反而会重新回到“画地为牢”、“固步自封”的境地。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下,“天朝心态”虽然是无知的产物,但毕竟还是真实的自得其乐。而在全球化的时代,试图在与西方绝缘的情况下建立中国人文学术的主体性,不过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作祟。这种情况下的“天朝心态”,就只能是掩盖自卑心理而故作高亢的惺惺作态了。所谓“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只要我们能够充分掌握中国人文学术的各种原始文献,植根于那些文献的历史文化脉络,深明其内在的问题意识,不丧失自家的“源头活水”,在这种情况下去充分了解海外的研究成果,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也就只会成为我们进一步反思自我的资源和助缘,不会成为作茧自缚的负担和枷锁。以上所说,正是我们选编并组织翻译这套“海外儒学研究前沿丛书”背后的考虑和自觉。是为序。
全部显示∨
白诗朗(John Berthrong),1946年生于美国威思康辛(Wisconsin)的La Crosse。堪萨斯大学文学学士(1969),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1972、1979)。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分别为道家哲学和宋代理学。曾在台湾进修中文(1974-1975)。曾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信仰问对话秘书(1980-1989)、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1985-1987)。现任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副院长、宗教对话研究所所长。除本书之外,还著有All Under Heaven: Trans forming Paradigms in Confucian-Christian Dialogue(1994).Transformations of the Confucian Way(1998)、The Divine Deli(1999),与Mary Evelyn Tucker合编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1998)。
全部显示∨
第一章 创造性、上帝和世界问题一 引论
二 修正版的怀特海式基元系统
第二章 上帝观的发展一 怀特海上帝观念的发展
二 上帝的构想:从《科学与近代世界》到《过程与实在》
三 从思辨体系的基本要素看《过程与实在》中上帝和创造性的分离问题
四 教父的插曲
五 协调的加入
六 谱写和谐的希望
第三章 南乐山的挑战一 南乐山论过程传统和上帝
二 南乐山论比较神圣性
三 南乐山论神圣实在
四 南乐山的本体论探索
五 南乐山论创造性和上帝
六 必然遭遇
七 基元系统、本体论、辩证法或形而上学
八 天涯若比邻
第四章 新儒家的引入
第五章 新儒家的插曲:朱熹论创造性一 新儒家的联系
二 朱熹的课程和资料
三 朱熹的创造性问题
四 过程之相似,结构之差异
五 连贯问题
第六章 再度统一的世界一 形式、创生和统一
二 “三元组”方案的焦点
三 形式、创生和统一
四 改良版过程哲学的构造图像
五 现实、潜能和合成
第七章 神圣事物的统一一 三位一体式回应
二 创造性综合
三 三位一体之爱欲
四 综合性原理和创造性
附录 构造分析(Archic analysis)的结构
参考文献
该书无电子版哦,想阅读点购买纸书吧,现在还在打折喔(⊙o⊙)